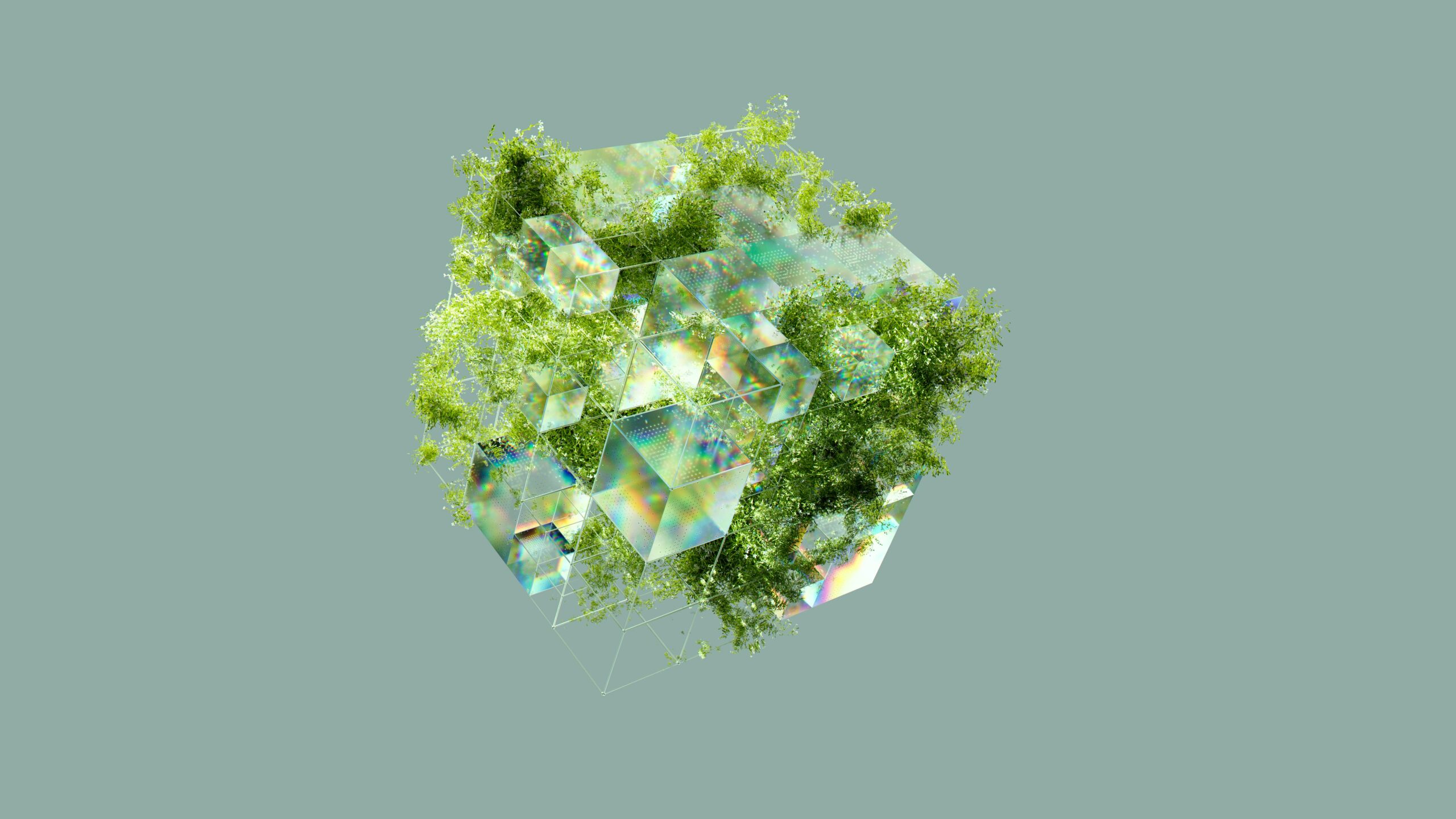1985年,当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写下《使女的故事》时,她曾觉得这个设定“荒诞至极”。那时的美国,在她眼中仍是“民主的理想典范”。然而近四十年后,这位加拿大作家在BBC采访中沉重坦言:这个关于女性被剥夺权利、沦为生育工具的反乌托邦故事,正变得“越来越可信”。
这不仅仅是一位作家的感慨,更是一面映照时代裂痕的镜子。当虚构的基列国阴影悄然逼近现实,我们不得不追问:究竟是什么力量,让一部科幻小说逐渐读起来像社会预言?
—
### 一、从“荒诞寓言”到“社会预警”:一个叙事的逆转
阿特伍德的创作初衷,本是对极端可能性的思想实验。她曾深入研究清教神权政治、20世纪的极权主义,尤其是将人口控制作为国策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。但她始终认为,这样的故事背景放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——直到历史开始转向。
转折点或许始于2016年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,阿特伍德多次公开表达忧虑。她观察到公共话语的极化、体制的脆弱性,以及原教旨主义思潮与政治权力的合流。书中那些曾被视为夸张的情节——比如女性被系统性剥夺财产权、工作权和身体自主权——突然在现实政治辩论中找到了诡异的回声:反堕胎法案的激进推进、关于女性“传统角色”的复古呼唤、对科学和教育的怀疑主义……
小说中最令人战栗的,并非赤裸的暴力,而是权利如何被一步步蚕食。基列国的建立并非一夕之间,而是通过紧急状态法、渐进的法律修正、对恐惧的利用以及对语言的重新定义(比如称强奸为“不正当交合”)来实现的。阿特伍德曾言:“没有哪座独裁大厦是一天建成的,它是一块砖一块砖砌成的。” 如今,我们是否也听到了某些地方砖块垒砌的窸窣声?
—
### 二、超越性别:反乌托邦的通用逻辑
尽管《使女的故事》聚焦女性压迫,但其内核揭示的是所有威权主义的通用蓝图。它关乎信息控制——使女们被禁止阅读;关乎历史改写——她们的过去被抹去;关乎社群瓦解——家庭纽带被强行割裂,代以严密的等级监控。
阿特伍德的深刻之处在于,她指出了极权并非总是以狰狞的面目降临。它可能包裹在“保护传统”、“国家安全”或“生命至上”的糖衣之中。基列国的创立者,正是利用了对恐怖袭击、生育率下降的普遍焦虑,以恢复秩序为名,推行了最野蛮的倒退。这种叙事策略,在当今全球各地的民粹主义浪潮中,我们是否感到似曾相识?
小说中,当主人公奥芙弗雷德试图回忆“自由以前”的生活时,那种记忆的模糊与疏离感最为可怕。这提醒我们:常态的滑移是悄无声息的。权利的丧失往往不是被夺走,而是在我们忙于生活、妥协、适应时,一点点被让渡的。
—
### 三、生育权:身体政治的终极战场
《使女的故事》将女性的子宫直接置于国家权力的管控之下,这触及了一个永恒的政治命题:谁拥有对身体的控制权?在基列国,生育不是权利,而是被赋予特定群体的国家义务。
现实中,关于生育权的辩论从未停歇,但近年来的激烈程度令人咋舌。从美国罗诉韦德案被推翻,到欧洲一些国家堕胎权的反复拉锯,女性的身体持续成为意识形态和宗教价值观的角力场。阿特伍德的故事之所以持续引发共鸣,正是因为它戳破了“科技进步必然带来社会进步”的迷思。即便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,身体的政治性反而可能被强化,成为定义“合格公民”的标尺。
这不仅是女性议题。生育控制背后,是权力对生命最本源领域的侵入。它关乎我们所有人:当国家有权决定谁可以生育、何时生育、为何生育时,人的主体性还剩几何?
—
### 四、我们的“可信”与“不可信”:在预警与行动之间
阿特伍德说故事变得“更可信”,并非断言未来必然如此。相反,这是一种文学的预警功能。反乌托邦小说的价值,不在于精准预测,而在于通过勾勒最坏的图景,激发我们的免疫反应。
我们与基列国的距离,取决于每一个社会节点的抵抗韧性:独立的司法、自由的媒体、活跃的公民社会、批判性的教育,以及最为重要的——普通人不愿妥协的日常勇气。奥芙弗雷德在书中说:“不要被灯红酒绿所蒙蔽,这下面是一片黑暗,暗流涌动。” 保持看见“暗流”的能力,正是避免噩梦成真的第一道防线。
历史告诉我们,人权不是一次性获得的永久资产,它需要每一代人的重新确认和捍卫。阿特伍德的故事如同一面高悬的镜子,照出的不是命定的未来,而是我们当下的选择所可能导向的深渊或坦途。
—
**最后,值得我们深思的是:** 当我们谈论《使女的故事》“越来越可信”时,我们恐惧的究竟是什么?是特定政治人物的上台,还是某种结构性倒退的浪潮?是女性权利的脆弱性,还是所有少数群体权利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?在这个信息碎片化、情绪极易被操控的时代,我们每个人,又该如何守护那些让“荒诞”止步于小说的现实壁垒?
**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思考:你从何时开始感到,某些小说中的情节不再遥远?我们时代最需要警惕的“第一块砖”,又是什么?**